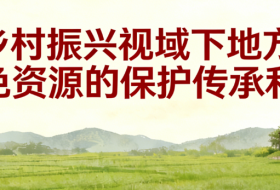红色教育下思政老师如何找回身份认同
红色教育浪潮里,思政教师身份认同危机与行动自觉觉醒交织,探寻重塑路径,筑牢育人根基。
“我是谁?” 这句看似哲学的追问,如今正卡在不少思政老师的喉咙里。红色教育的大幕拉开后,课堂被期待成为火炬,老师却被要求同时扮演点火者、护火人、传火者三重角色。多重期待叠加,身份认同像被拉长的橡皮筋,随时可能断裂。
断裂的声响最先出现在课堂。过去,思政课可以四平八稳地讲条文,如今学生掏出手机,一条短视频就能把宏大叙事拆成碎片。老师若仍用旧脚本,学生便用沉默投票。沉默背后,是身份感的流失 ——“我讲得越用力,他们离我越远”。

红色资源本该是粘合剂,却也可能变成新的裂缝。某地校馆合作,把旧址搬进教室,老师被安排站在展柜旁讲解。灯光打在文物上,也打在老师的尴尬里:他成了讲解员,不再是课堂的主导者。身份被场景稀释,行动自然跟着迟疑。
要缝合裂缝,得先承认裂缝存在。身份认同不是文件上的职称,而是 “我为何站在这里” 的持续回答。红色教育提供了回答的新角度:把 “我” 放进 “我们” 的历史纵深里。当思政老师把家族长辈的支前故事嵌进课程,条文突然有了体温,学生抬头,老师也重新听见自己的心跳。
行动自觉的启动键,藏在 “共情” 而非 “共训” 里。共情需要老师先卸下 “真理代言人” 的盔甲,承认自己也曾被信仰问题刺痛。某次讨论,一位老师坦白:“我爷爷临终前才告诉我,他当年也动摇过。” 话音落下,教室安静得能听见粉笔灰掉落。那一刻,师生同时成为追问者,红色教育从宣讲变成对话。
技术不是敌人,是放大镜。短视频可以拆叙事,也能重组叙事。老师把旧址的口述史剪成三分钟短片,配上一句 “如果你在场,会签那份生死状吗?” 弹幕飞过,答案各异,但 “我” 与 “历史” 的距离被拉近。技术帮助老师完成身份迁移:从讲述者变成提问者,从答案供应商变成思考合伙人。

评价体系的钝刀也得磨。当考核仍把 “到课率”“抬头率” 当硬指标,老师难免把红色教育做成打卡表演。某校尝试把 “学生课后写给十年后的自己的一封信” 纳入考评,信里出现最多的词是 “我想成为像你一样追问的人”。老师收到回信,第一次感到评价在反哺认同。
红色教育的终点不是让学生记住多少事件,而是让他们在离开教室后,仍愿意把个人命运与更大的人群相连。思政老师的身份认同,也不取决于他背熟多少金句,而取决于他能否在每一次课堂震荡中,重新确认:我站在这里,是因为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寻找答案。